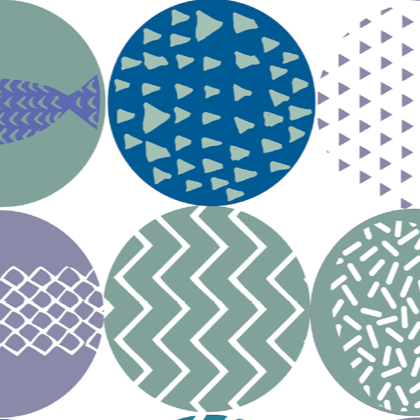现象学与现代艺术:现代主义与前卫艺术的起源
本文讨论现代主义的兴起,另以德勒兹理论为讨论的基础,并将此问题同“前卫”的概念联系起来。“现代主义”和“前卫”这两个术语,常被人用作同义词,虽不严谨,但一样用来指那些或新或怪的现象,只要不符合业已建立的秩序便是。不过,这两个术语实际上并非同一,而是各有历史内涵,其意义是变化发展着的。其中要义是,两者的不同在于前卫的概念蕴含着艺术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且是从现象学角度所重新理解的关系。
当然,若要全面讨论这个问题,需要写一整本书才行,所以本文只勾勒一个可行的思考框架,以便为进一步研究打下基础。为此,我得先解释现代艺术所具有的一些共性特征。这样,本文的第一部分将讨论一个在几何透视(数学透视)中与生俱来的因素,即主体和经验客体的“本体相关性”,并在浪漫主义的艺术实践中及其各种内在冲突中,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本文第二部分将讨论印象主义兴起的决定性因素,这是现代主义的关键。我认为,塞尚、高更及其同仁的艺术标志着重要的转折点,对他们来说,艺术的符号象征功能在于卷入了本体相关性的转变,而不仅仅是体现了这一转变。本文的第三部分即讨论这一转变,及其所促成的20世纪艺术的各种形态之变。
一、透视法与本体相关性
首先,几何透视是一个图像设置法,其承传并不单纯,而是在画面设置的理想化历史进程中,作为理论和体制之整体的一部分而承传下来,有如音乐中的“学院”传统之承传。几何透视的传统,来自古典文化理论和意大利文艺复兴。用哲学术语来说,学术观点必须符合“永恒”的经典理论,这是理性建构的重中之重,而几何透视则是经典理论的一个范式。对这一学术权威的突破,是一个复杂而持续的过程,至少开始于启蒙运动时期,并与经济和社会的变革密切相关。只不过在古典传统内部,有一些因素扰乱了这一进程,其中之一便与几何透视相关。就此,请看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的说法:
照潘诺夫斯基(Panofsky)的描述,通过透视而获得的新空间“使客体对象化了,同时也使主体人格化了。”莫非这不是一种准备突破陈规的激进方法?凭了这一法,主体决然脱离了对象世界中的客体。主客体的分离使我们得以面对世界,去准备更进一步的突破,突破自我生命中业已预设的终点线,因为我们已不再默认那条终点线。主客体的分离使人能够克服自我从属于外部世界的意识。自我与外界之间界线的缺失,来自前现代的宇宙观,即古典传统。[2]
这个观点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是透视效果以视觉关系而连接了观看者与被观看的固定的对象世界,另一方面是在二者间制造了距离,使观看的主体得以质疑主客体之间的关系。这样一来,透视问题便在大体上可以用来质疑主体与经验客体之间的关系,而这一关系是笛卡尔以来欧洲哲学的主要特征,并深深卷入了现代社会最常态的政治和社会变化。
当然也有另一种情形,这就是19世纪的艺术倾向总与浪漫主义相伴随,也总与主客体关系相伴随。不过这当中还有一个连接,也颇有意义。为了把握这个连接,我们必须留意一个貌似极为一般但却十分重要的连续性,这就是启蒙运动以来另一条哲学发展的线索。按照这一哲学思路,经验中的主客体关系,并不是一者被动地给予另一者,而是互动互予的,并在这交往的过程中,双方都有所改变。
由此观之,世界的主观结构和客观结构具有直接的交互关系,要言及其一,便必得言及另一。我将这种一般性认识称作“本体相关性”。在德国的唯心主义哲学传统和柏格森(Bergson)的生命哲学中也包含着这种认识,二者皆认为思想结构和客观世界是相互界定的。尽管这种交互性可能很松散,但却是存在主义现象学的基本哲学特征,尤其是梅洛·庞蒂(Merleau-Ponty)现象学的特征。对于人的主体性而言,这特征是一种时空结构,它使人的主体性成为有限的存在。于是,一个共识便由此产生:经验中的主客体关系是主动的交互性关系,而不是静态的协作关系。
这个共识一旦涉及到历时性,就变得激进起来。这就是说,时间不仅仅是经验的必要条件,而且也是对经验之含义的深刻质疑。在此,变数、无常、历史转型等概念,皆具有主动意义。若要理解视觉艺术中的这一意义,我们就必须转回到几何透视的模糊含义中,回到主体与客体经验的关系中。这是对19世纪学院派正统观念的挑战,先起于哲学,接着出现在艺术界。对此我们有许多例证,例如普桑式艺术(Poussinisme)同鲁本斯式艺术(Rubenisme)的异质性,便在学院派传统中不断出现。或许,安格尔与德拉克洛瓦的冲突,是这异质冲突的高潮。
安格尔是官方认可的艺术家,他强调造型的准确和严谨,以及画面的完成感。安格尔是理性的,近于古典范式及其视觉秩序。相比之下,德拉克洛瓦更自由,尤其是在构图和用色方面,以及所绘内容的选择方面。若是仅在浅表的辩证层面上来说主客体之间的冲突,那么可以说安格尔承续了客观世界的秩序和道德观念,而德拉克洛瓦则站在了主观的一边,他质疑主体同外部世界的关系。
这两者当然各自都占有某种真理,但重要的却是这两位艺术家将真理蕴含于艺术中的方法。虽然安格尔得到了官方认可,但这并不是说他不冒风险,例如他对裸女和东方题材的偏爱,便有情色之嫌。这是安格尔的主观的性幻想,与他同时代的学院派画家一样,他的情色反映了公共道德与个人趣味的冲突。
那么德拉克洛瓦就更不用说了,他的性幻想以及随之而来的风险贯穿了他的整个艺术生涯。但是他也有传统的一面,例如《后宫之死》一画采用了传统构图,画面结构是对角线式的。这就是说,德拉克洛瓦在处理历史题材时,遵循了学院派的原则,哪怕并不是严格遵守。有鉴于此,安格尔和德拉克洛瓦所展现的所有细节及其影响,都需要更充足的分析。不过,我已经充分揭示了此中危机,而不仅仅是此中冲突。
安格尔与德拉克洛瓦之间的冲突,不止于风格和体制的不同所造成的主客观冲突,而更在于二者的对立,这实际上使其立场和观点的冲突内在化了。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冲突之所以发展成危机,是因为双方的冲突既尖锐又摸棱两可,结果,这双方对立的内因和语境反而被忽视了。这一情形的结局被延长,也被间歇性地打断,从而促成了现代主义的兴起,影响了随后的现代艺术发展。从现象学角度说,这与“本体相关性”有着重要的依存关系。
二、从印象主义到现代主义
要理解这种依存关系,我们就得将早期现代主义画家们之“完成感”的缺失,同其透视感的弱化联系起来。例如在马奈、莫奈、毕沙罗和西斯莱的作品中,视觉感知和情感反应的即兴特征,总是同他们不愿遵从传统艺术的陈规息息相关。
这当中总是存在着历时性,例如画面效果中稍纵即逝的动感和氛围。然而更重要的是,这一效果必然与城市生活的节奏相关,无论是工业产品还是手工艺品,无论是尘嚣的律动还是享受闲暇,抑或是在公共空间偶遇,其中皆蕴含着生活的历时节奏。当时的批评家埃德蒙·杜然迪(Edmond Duranty)在1876年推出了一本小册子《新绘画》,书中提出了这个问题:
通过窗户我们得以从室内看向室外,窗框永远与我们相伴。窗框的剪裁功能与我们离窗户的远近有关,与我们或坐或站有关。窗框所剪裁的户外画面,会出乎意料,会使画面各不相同。窗框总是给予我们无尽的变化和意外的惊喜,这是现实所能奉献的一大乐趣。
在这段引语中,杜然迪所言,是窗户的字面意义和隐喻含义。在个人与外部世界的相关性中,无论是字面还是隐喻,窗户的功能确认了知觉的主观状态及其重要性。接着,杜然迪将自己的窗户之喻引向了街市的喧嚷和自然的律动,并同印象主义的新绘画联系了起来。他写道:
这些画家们尝试描绘街市人行道上行人的摩肩接踵,及其动感和震颤,就像他们描绘树叶和水面波纹的颤动,以及天光云影下大气的颤动,他们也在阴沉的天色下捕捉晦涩的阳光和微妙的彩虹之色。
在这段论述中,杜然迪指出了印象派画家所描绘的城市同他们笔下的自然之间的连续性。这种连续的关系,也是短暂易逝的景象同流动的观察者之间的关系。视觉图像的这一诗性特征,不是通过抽象的冥想或置身度外来获得的,而是乐于介入、长期专注的结果,唯其如此,方能捕捉景观的多样与微妙。
关于这一点,马奈作于1863年的名画《草地上的午餐》(现藏巴黎奥赛美术馆)可以用作说明。当然,此画的绯闻来自作者在画面上并置了一丝不挂的裸女和衣着欲盖弥彰的半裸女,以及穿得一本正经的两位风流倜谠的男士。除了性处理的挑衅性,这幅画实际上还有节制地预发了野兽主义和表现主义的“出生证”。这幅画对现世生活的描绘,不符合当时历史题材和古典趣味的要求。
不过,就我此处的论题而言,我想强调的是别的方面。这幅画笔触明显,而非抹光涂匀,画家没有去追求所谓的视错觉,画面上有些地方甚至没有画完。在这方面,此画呈现了德勒兹所认定的现代绘画的关键特征,即所谓物质基础或“图解”(diagram)的特性。但是,这一特征却又及其晦涩。我们可能会以为这样的画面处理经过了深思熟虑,其实不然,这一特征正好推翻了我们的自以为是,而呈现了画面的杂乱无章。
马奈画面的不稳定感很强,空间安排无序而散乱,例如那位半着衣的女子,虽然身在后面的背景中,但看上去似乎离前景太近,结果因其动势和位置而与画中的主要人物搅成一团。这种不稳定的视觉效果压缩了画面空间,制造了平面感。那么,我们在此要强调的究竟是什么?是凝视,若用思辩的话来说,我们需要关注画中这群人的动态凝视。
画中裸女看上去正凝视着画外的观画者,而正面坐着的男子则看向别处。两人都与观画者互视,但右边的男子却侧身趋向自己的同伴,并盯着他们。在观画者眼里,这是视线的“失谐”。同样失谐的是,那位半着衣的女子看上去完全游离于自己的处所,不知身在何处。对于马奈有意制造的这一不谐,我的观点是:画家意在招唤画外的观画者参与进来,加入在场的画中人。因此,若说这幅画没有同时再现进行时态的瞬间和过去时态的瞬间,那么,观画者却已然或正在将自己同画中人联系起来。这就是说,此画在构图上的失谐,暗示了视觉接受的即兴特征和瞬时性,造就了看与被看的交互关系。
其他画家也有类似情况,但其视觉关系的即兴特征和瞬时性,在风格上却有所不同,例如莫奈的《欧州之门,圣拉萨勒火车站》(1877,巴黎玛蒙腾博物馆)。在视觉效果上,这幅画里的人物和机车,日光和蒸汽,都获得了形体和块面的平衡,尤其是画中的团团蒸汽,既将观画者的视线引向远处,同时又提示了一个反向运动,将远方引向观画者。这个双向运动具有认识论的蕴含,暗示了主客体之间的经验关系,二者不是绝对割裂的,却是根据新的情境而不断变化的。换言之,主体及其所经验的周围世界是不断互动的,并在互动中调整相互关系。
塞尚也是这样一个好例子,恰如本书将在第四章讨论的,互动关系不仅实实在在,而且更加复杂。塞尚自1870年代以来,渐渐发展了一种新画法,他在画面上并置小色块,而不是强调色调深浅的不同,并以此造型。说到绘画造型,塞尚的方法并不影响画面效果的统一性,即便将不同视点引入同一画面,他强调的是所绘对象的造型特征,旨在增强其可塑性。于是,此处便产生了潜在的三方协调:画中所绘对象的造型特征、所绘对象的完全在场性、观画者在观照这两者时其视点的可变性。在谈到这一复杂性时,艺术史学家克拉克(T.J. Clark)有一段深刻而精彩的论述:
在塞尚的艺术中,“观看”的确定性有二:一是色彩以及色彩所塑造的对象形体,二是观看可以拥有世界,包括所看世界的全部及其细节,哪怕这个世界局限于所见的视域。然而诡异的是,不确定性也与时俱增,尤其是观看过程中被看事物的分离和连接关系。于是,再现的任务便具有了双重性:一是将眼前的世界展示为确定无疑的实在世界,二是同时也承认观画者的无知,因为观画者无法以自己的视觉感官来使对象世界确定无疑。
视觉世界是由看画者和被看对象的相互关系来界定的,然而图像再现却难于仅以画面效果来企及这一点,因为视觉因素只是诸多因素之一,交互的主客体关系不仅涉及感官,还涉及我们身体的的物理特性和处身于其中的社会环境。克拉克接着说:“这样,塞尚将绘画从视觉领域引入了意识形态领域,观看不再仅仅是关于观看的自身行为,不再是关于自身之真理的行为,而且还是通向自身的行为,涉及了这一行为的临界点和突破点。”
这里所说的突破点当然以几何透视为中心,暗含着看画者和被看的图像之间的连续性,这在象征的意义上将作为大自然之观照者的画家和被理想化了的观照对象连接了起来。所谓理想化,是赋予观照对象以秩序。当然,这种静止的单向性关系,与历时的视觉复杂性并不协调,因为历时性不仅涉及被观照的对象,还涉及其他的相关因素。
因此,如果艺术对视觉世界的创造性介入是一种探索,那么在逻辑上便会要求出新,也就是对图像再现之道进行激进的变革,即在语义和句法上的符码变革。这是观照经验在主客体之间所进行的本体性互动,这是探索变革的机会。
于是,塞尚的成就便从图像的层面延伸到了更宽广的文化意义的层面,这使得“意识形态”不再是一个负面概念。这样的转变不仅见于塞尚,也扩散到高更及其周围的人,主要是梵高和高更本人。在他们的作品中,形式、轮廓、色彩等因素的制式感较强,并在随后被野兽派和德国表现主义及其他画家们进一步强化了。这既是一种自我解放,也是给世界的表现以更多的可能性。这种尼采式的解放,极具现象学特征。对于更激进的艺术家们来说,这样的解放因其类似于乌托邦的性质而获得了政治和社会性的蕴含。
由此,“视觉的意识形态”将我们引到了质变的门槛上。现代艺术家们的图像策略不仅是完善对真实世界之历时常态的描绘,而且将艺术本身当作观照的对象来体验,以直接的绘画行为去理解真实世界的独特性。现代画家们对平面性的强调,便是对这种独特性的不声不响的体验。
于是,机会之门便向语义和句法结构打开了,超越几何透视传统的激进变革已经有了迹象。关于这一转变,需要强调是,这不是一次性的进化,而是一个不断的进程,是一点一滴积累的进程,是一个持续修正的进程,其前进目的地是新的可能性。
这是新与旧互动的复杂进程,经过长时间的积累,终于由量变到质变,发生了激进的变革,例如毕加索画于1907年的《阿维农的少女》便展示了这种剧烈变革。有了这样的前提,“前卫”一词的专属性便获得了保障,被用来专指变革的发起者。这里的关键不是再现现实的新方法,而是探索再现与现实之间各种可能的新关系。在现象学的意义上说,前卫艺术所蕴含的,便是对这些新关系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