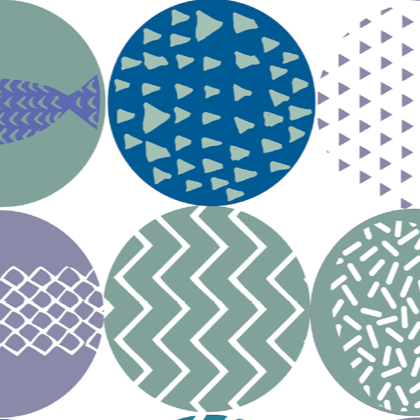艺术乡建只是艺术家的乌托邦梦想吗?
近日,在北京中华世纪坛展出的《中国艺术乡村建设展》集中展示了在艺术乡建领域活跃的专家左靖、渠岩和靳勒的乡建项目。
近年来,艺术乡建已经是中国当代艺术领域最热的话题之一。去年,日本北川富朗主导的越后妻有大地艺术节将这一热度推向高潮。到乡村办展览、举办艺术节已经成为中国众多策展人和艺术家喜闻乐见的一种方式。
乡建并非是今日的产物,在中国20世纪早期,就有一大批学者开启了对中国乡村建设的实践。但是近年来的艺术乡建却只有十几年的历史。其中左靖、渠岩和靳勒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三人中渠岩和靳勒是当代艺术家,左靖是策展人,三人都辗转于城市系统的画廊、美术馆和高校的专业艺术圈。
后来,左靖偶遇了安徽的碧山村,渠岩邂逅了山西的许村,靳勒回到自己的家乡——干肃石节子村。他们敏锐地发现了乡村的价值和艺术新的可能性,他们在这些保留着传统人文特色的村庄里得到了启示,找到了事业的方向。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放弃优渥的城市环境,常年扎根在边远的村庄耕耘。




本次展览,三位乡建者带来了四个地理环境完全不同的乡建项目。左靖从2011年碧山村开始,迄今已经开启了三个项目,这次展览是他在云南景迈山的项目。闻名遐迩的景迈山普洱茶就产于此地,这里也是布朗族,傣族聚居地,具有典型的云南风情。渠岩带来了他的成名作许村计划和从2016年开启的广东青田计划。许村是晋中山西的一个村庄,保留了大量明清时期的建筑。青田村四面环水,是广东顺德地区的一个水乡。而靳勒的作品就是2009年创建的石节子村美术馆。石节子村位于中国甘肃天水附近,周边环境是典型的黄土高原干旱地区。
三位不同的艺术乡建者
左靖、渠岩和靳勒作为资深的艺术乡建者为各自耕耘的乡村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他们在乡村中建设了很多文化设施,举办了多项文化活动,使这些原本默默无闻的小村庄成为了社会的焦点。同时,三位乡建者的理念和实践方式上也有各自不同特点。

靳勒具有双重身份,他本身就是石节子村民,之后他去了大城市走上了专业美术的道路。石节子村没有优美的自然环境,也缺乏悠久的历史,但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都牵动着靳勒的情感。靳勒的艺术乡建非常明确,就是以艺术带动乡村发展,让艺术给家乡带来活力。靳勒将这个小山村里13户农家都变成了美术馆,村庄的山水、田园、植被、院落、家畜、农具和日用品都成为了美术馆的展品。他邀请众多的艺术家来到这里驻地创作,而乡民也参与其中。石节子村曾经做过一个活动,即外来的艺术家们和村民们一起做艺术创作,题目是:“我们一起飞”。这次展览中,石节子展区搭起了一个农家小屋——女女馆,这座小屋还原了石节子农家美术馆原貌。土炕、饭桌、小木柜、烧水壶、墙上的镜框和奖状、这些西北山村的生活元素,带给城市观众真实的触感。

渠岩的项目——许村和青田村虽然是一北一南、山村与水乡完全不同的村庄,但贯穿其中的是渠岩对乡村传统文化价值的追溯和复兴的理念。许村和青田村都是从古代到现代具有历史线索的建筑和民俗生态的乡村。渠岩著名的“青田范式”正是从传统乡村的历史、环境与人文等九个方面以现代视角对乡村系统做了全方位的梳理。从许村的艺术乡建到青田的去艺术化,渠岩的乡建超越了一般意义的艺术乡建,构建了一个以尊重传统文脉为依托的体系化的乡建系统。

左靖的景迈山项目接近人类学的研究方式。展览中,景迈山的布朗族、傣族的日常生活、节日、赕佛、自然环境都有详尽的介绍,其中,古茶林的植物群落和当地人使用的蒸酒器、石磨、舂米机、村寨的样貌都用彩绘详尽描绘,仿佛是一本本丰富的绘本博物志,这样通俗易懂的方式对于乡民理解自己的环境与文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左靖的第一个艺术乡建项目——碧山计划,是一个具有完整社会理念的乡村共同体计划。在后期的乡建过程中,左靖的乡建道路转向对乡村文化进行全方位田野调查与专家型研究建构的方式,这在他出版的《碧山计划》丛书与《黟县百工》,以及贵州茅贡镇和云南景迈山展览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对传统乡村价值的肯定与保护
虽然三位乡建者的项目各有不同,但是三者也有很多相似之处。其中对传统乡村价值的肯定与保护是三者的共同特点,这从他们对老宅的保护就可见一斑。全球现代化所带来的一大副作用就是地域文化和传统生活方式的逐渐湮灭。在中国这一问题尤为严重,一般情况下,中国的乡村中只有具有文物价值的地区才会得以文化遗产的名义进行保护,但这种保护令其脱离日常生活化,成为死去的文化标本。另一方面,一些商业项目包装出一些伪传统民俗活动也破坏了真正原生态的传统生活。而三个乡建项目所呵护的传统是活着的传统,是与同质化严重的城市现代化生活所相异的生活方式。这是艺术家对于当今秉持快速发展这一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反拨。无论何时,传统的乡村生活和差异化的地域文化不仅是我们记忆的保存,也是我们当今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从精英艺术到群体艺术
从另一个角度出发,三位乡建者的当代艺术家身份决定了艺术乡建是一次与当代艺术密切相关的行为。
发轫于西方的现当代艺术,从开始就有两大对立的思想,一是反对艺术与生活的截然对立,主张向生活无限开放的艺术;二是主张艺术要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不依附于生活的领域。这两大传统在西方的发展都蔚为大观,前者在20世纪70年代用波普行为艺术,身体艺术,观念艺术以及情景国际主义、社群艺术来打破传统的精英艺术,让“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在这些观念召唤下,艺术不仅可以从单纯的艺术领域走向广阔的生活,个人艺术家的创作也可以参与到群体创作行为中。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艺术以体制叛逆者的形象登上历史舞台。当代艺术在中国大获成功之后,也逐渐成为国际资本和富裕藏家的宠儿。当代艺术的形式越来越丰富,但其本质的先锋性和对社会的反思力度在某种程度上却在减弱,早期叛逆的当代艺术家成为资本规训下的艺术生产者。当代艺术被禁锢于城市系统的画廊、艺术市场、工作室、艺术研究机构链条中。
在这样的背景下,当代艺术既无法遵循艺术向生活开放的的态度,也无法真正实施艺术的自律性。而艺术乡建这种在中国当代艺术链条之外的行为,就打破了原有的界限。它的发生地在乡村——与当代艺术原发地的城市系统完全不同的区域。同时,参与乡建的艺术家也不再是个体精英角色,而是集体行为的参与者。在乡村中,艺术不再是一个供人观赏的美丽花瓶,它成为了向生活延伸的多主体发生的“剧场”。正如渠岩在“青田计划”中提到的多主体概念——村民、新乡贤、村委会、镇政府、研究所、企业家和艺术家。石节子村提出的口号“我们一起飞”,都表明艺术乡建成为了多个社会角色自觉自愿的集体参与行为。在这里,艺术也承担起了一定的社会职责,成为了社会转型期内沟通和弥合城乡文化差别的协调者和建构者的角色。
艺术乡建成为了中国当代艺术的一次重要的分流与转折。
城市与乡村的双向救赎
谈到艺术乡建,人们潜意识里都会理解为城市对乡村的建设和文化输出。留守的乡村人困守于贫瘠的土地和有限的物质条件,城市在物质和知识财富上拥有远比乡村丰富的资源。
乡村相比城市,也有自己的独特优势。和慢节奏的乡村相比,城市更像一个高度紧张,快速转动的机器系统。城市的空间是逼仄局促的。城市人工作紧张,充满了焦虑压抑的情绪,被消费文化和过度信息所裹挟,人的神经时刻被调动和牵引,难有片刻宁静。
城市也是一个被经济发展高度控制的社会空间。人群的社会形态完全按照生产单元严格划分,城市人在公司——家庭两种模式中机械的切换,城市人看似自由,其实只是扮演着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双重角色,缺乏文化建设的主导性,这也是城市人幸福感偏低一个重要原因。
来自城市的乡建者对乡民的知识和审美输出,对乡民来说带来了全新的世界。乡村的慢生活和广阔的自然环境也对城市人来说不啻于一种心灵的治愈。同时,乡民的生活和工作并没有被现代城市系统所主宰,仍然有相对空闲的时间,加上乡民丰富的自然知识和农艺技能,这些条件为城市乡建者与乡民共同创建富于情感的社区文化和充满想象力的社群生活带来了丰富的可能性。
不同的社群在乡村空间的交融碰撞会带来全新的可能性,不同族群在共同生活工作中,身份标签将变得不再重要,艺术家学者得到了多种乡村知识和技艺,乡民的才智也得到了释放。这场在乡村的社会实验所取得的经验,不仅将有利于乡村的建设,最终也将反哺于城市文化建设。
艺术乡建只是艺术家的乌托邦梦想吗?
近年来,伴随着中国艺术乡建的热潮,对艺术乡建的非议也很多。其中最常见的意见就是认为艺术家的乡村建设只是艺术家的美好想象,乡村的经济建设才是拯救乡村的最根本出路。这一思想甚至也困扰着很多艺术乡建者。笔者认为,经济当然是乡村发展的根基,但是乡村的文化建设也并非无足轻重。需要指出的是,之所以中国大部分的城市民众和知识精英一致把经济列为乡村发展的首要甚至唯一因素,这是受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传统思维的影响所致,在这样的逻辑下,乡民和低收入者只有先解决经济问题之后,才可以谈论文化建设的可能。
这种思维逻辑存在着很大的弊端,首先,中国的乡村具有多样性,虽然大部分乡村的物质条件较差,但少部分富裕乡村的经济发展并不逊色,就像这次展览中展示的广东青田和云南景迈山地区,两者凭借着各自优越的自然条件,乡民的物质生活较为优渥。



另一方面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思维逻辑,忽视了人作为主体性的其他需求。很多从没有去过乡村的城市人主观的认为村民没有欣赏艺术的能力。在他们眼中,村民只有现实利益的需求,是缺乏知识和懵懂的。但是,当人们看到展览中四个乡村村民对乡建活动的参与盛况,以及许村村民王仲祥丰富多彩的绘画和景迈山文艺青年丹依章阅读的书籍、自己设计的美丽贴纸,我们就能强烈感觉到乡民和城市人一样充满了对美与知识的渴望。城市人要放下自己优越的视角,以平等的姿态看待乡村与乡民。
艺术家主导的乡村建设显然不同于政府和企业的乡村建设路径。艺术家的乡村设想难免有过于理想化成分,这不能苛责于艺术家,艺术家也不应该承载过于沉重的负荷,艺术乡建也不具有广泛的复制性,艺术家应该扮演好当地的文化组织者的角色,政府和企业更多的从乡村的政策制定、硬件改善和经济发展角度出发,而乡民也要尽力改变从属的角色,积极发动起来,参与文化与经济建设的活动中,只有各方发挥自身的优势,才能为乡村建设赢得更好的发展前景。
我们要正视乡村建设的问题,但宽容远比苛责更为重要。我们正处于乡村建设的初期发展阶段,未来充满了无限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