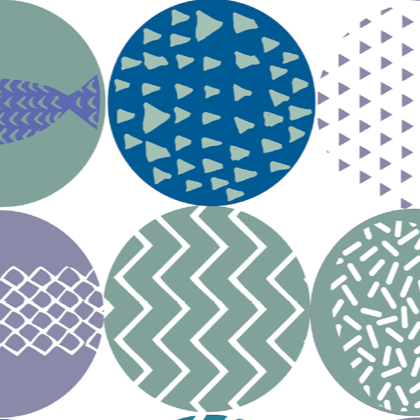夏托 :美学的困惑
我这里要谈论的是美学的困惑,并以交替的方式,常常也是相关的方式,给这个美学术语赋予接受理论和创作理论的意义。且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困惑:美学家一直被夹在这两个极之间!因此,有时候他的读者有些不知所措。美学就是这样,是一位雅努斯神——但是除了他的两个面孔之外,雅努斯还是打开通道之神,守门之神。两道门在美学家面前打开,他有时候想违背任何逻辑,同时跨过这两道门!他这样做也许会被绊倒......
人们必须适应这种合理性的缺乏,这种先天不足。在这一点上,我的看法是这样,美学的两个极不应该混为一谈,而且正因为我们没有将它们混淆,这两个极可以更好地相互合作。这一点尤其涉及到美学中的某个部分,即可以被称之为艺术美学的那部分,尽管这种说法显得冗余。我想说的是,美学超出艺术的范围,因为作为一种接受理论,美学也被应用于其他对象(风景、设计、时尚等),同样,艺术的定义并不仅仅局限于美学的概念,因为艺术呈现出某些区别于其他文化实践的独特性,当然还有一个地方,在那里,两种语汇相互交汇,恰恰是可以找到艺术特有的美学价值的地方。
第一种方法:从艺术的接受经验谈起
困惑(trouble)属于这些思想的范畴,其定义与它们所指定内容的不可定义性相互冲突。但是这种指定可以分为两种——通过将其这般地分割,我们着手开辟其定义的道路。困惑,它一方面是指含混、模糊,例如模糊的目光;另一方面是指不确定、两面性,例如人格障碍。当然,我们可以在其中一种困惑中看到另一种困惑的特点……反之亦然。模糊的目光在看到某样东西时却视而不见;有障碍的人格性情不明、无法区分。首先,我对第二类情况更感兴趣,时而也不会忘记第一类情况,然而其目的是要确定美学态度的特点,把它看作两极之间令人困惑的摇摆。
关于两极性的看法
毫无疑问,我们可以从精神分析方面,从人们所说的双相障碍(或躁郁症)方面来谈这个问题,双相障碍的主要症状是患者反复出现亢奋期和抑郁期。我们同样可以将由依赖状态诱发的边缘性人格障碍归于这一方面,这种依赖状态“一只脚踏在精神病的范围,一只脚踏在神经官能症的范围”1,精神分析学家爱德华·格洛弗(Edward Glover)如是写道。至于这种状态,即时而镇静时而中性的状态,问题不仅仅在于衡量它们与“正常”状态和病理状态这两个极之间的关系,还要对正常和病理进行思考。格洛弗继而说:这种状态“源自于妄想狂状态,尽管偶尔会主要表现出抑郁症的症状。然而,这种状态在发展过程中充分表现为神经官能症,因此与合理的现实性存在联系,当然,与毒品的关系则是一个重大例外,在毒品背后隐藏着妄想狂机制”。
神经官能症在这里被视作正极,与精神病这一负极相对,因为现实原则在此仍然占据主导。因此,神经官能症或许是一种良性的人格障碍,因为它并不导致与现实的断裂。神经官能症患者对存在是有意识的,他管理着冲动,将其引向欲望和阻止欲望实现的折中方向。人们可以想象有不同程度的症状:纯粹的神经官能症或精神病、在两者的边缘、介于两者之间、或多或少地偏向前者或后者等。弗洛伊德说,艺术家“极近神经官能症”,而艺术是“引导人们从幻想走向现实的回归道路”2。这种神经官能症让人们幻想另一个世界,在那里,所有的幻想都如愿以偿地得到满足,所有人都有这样的症状,只是在某个“活跃着极强烈冲动和倾向”的人身上更为剧烈而已,这个人将成为艺术家。那么这个人与大众症状有什么区别呢?就在将幻想定形于假想的世界中,这正是艺术家的特权,原因一方面在于他有这种假想的能力(才干或天赋),另一方面在于他得到公众的认可,公众自身也有神经官能症的症状,但被局限于“难得做做白日梦的满足之中,而且他们还得意识到这些白日梦”。
更准确地说,如果弗洛伊德这样说,艺术家是“极近神经官能症的内倾型的人”,那么我们应该指出,对一个内倾型人来说,至少按照精神分析学家的意思,他与外界相处得极为融洽,既可以借助其作品的成形,也可以借助另一事实,即该作品“是他人的快乐之源”。这两个条件均不够充分,却也必不可少。无论如何,重要的是现实两次介入到艺术的可能性中:创作学(poïétique)方面,即创作方面3,以及美学方面,即接受方面。但我们可以补充一点,这两个方面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提出的看法,在艺术创作中,有一个美学时刻与创作学时刻的相互冲突——在这一点上,我记起了关于米罗(Miró)的美妙电影,在影片中我们看到他既绘画又雕塑,然后注视他正在进行的工作,最后回头对作品进行修改或拓展4。艺术家,不管他说什么,都不能略去美学……在第二部分中必然会再谈到这个主题……
格洛弗的说法可以用于表达这种思想:“一只脚踏在这儿,一只脚踏在那儿”,可以有不同的变体:一只脚踏在想象中,一只脚踏在现实中,一只脚踏在神经症中,一只脚踏在现实中,一只脚踏在主观性中,一只脚踏在客观性中,一只脚踏在社会之中,一只脚踏在社会之外,一只脚踏在创作学中,一只脚踏在美学中,不一而足。我们在科克托笔下准确地找到这种说法,他断言,艺术家就像跛脚的天使:
“确实,他们的身躯完全适应于狗狼难辨的状况,而我就生活在这种状况中。人们很难更好地定义出这般顽强,凭借这种顽强,我小心翼翼地踩着那块并不给我带来丝毫信心的土地。我一只脚行于地面,一只脚悬于空中。而这种跛行使我确信,天使们也蹒跚而行,也就是说一瘸一拐地行走,或许你更喜欢这样说,一旦他们不再飞行,就会笨拙地行走。5”
“狗狼难辨”:又是一个双重性的程式,以及可能相关的困惑。“介于狗和狼之间”的表达指的是一天中昏暗的时刻,傍晚或清晨,使得我们很难将一只狗与一匹狼区别开来。有趣的是我们还要指出,这个表达中包含的未区分状态与两极性相关,狗象征着白天,狼象征着黑夜。在另一种文化中,我们可能会谈及对立面的互补性,比如阴和阳(黑/白,女性/男性,月亮/太阳,负面/正面),“阴”指的是(山的)阴面,“阳”指的是向阳面。我们是否可以说诗人一只脚踏在阴的范围内,一只脚踏在阳的范围内呢?这又可能引出一个范例式分配:阴是阳的介质,而阳是阴的动力。
在这里援引弗洛伊德的暗恐理论(das Unheimliche)貌似平淡无奇。除了我们可以从这一理论中诠释出的所有内容,这里的援引还有一点理论上的原因,弗洛伊德曾做过明确说明:“(……)在详尽的美学著作中,我们似乎找不到任何关于美学的内容,这些作品往往更倾向于阐释积极、美好、高尚、动人的情感,以及那些激起消极、恶劣或痛苦情感的境况或事物6。”这个断言并不完全正确(例如当我们想到伯克或雨果时),但它还是不无作用地提醒我们,美学并不是仅仅有关积极的价值观,也不是仅仅有关和谐,更不仅仅是浅显易见的阐述。弗洛伊德再次提到谢林对于恐惑(unheimlich)的定义:“所有应该保密、隐藏,但却显现出来的事物”7,并将其与“‘heimlich’一词含义的双重性”作对比,发现“最后‘heimlich’一词与其反义词‘unheimlich’意义重合”8。熟悉和隐秘两层意思均包含在heimlich一词中,所以我们发现它的含义接近反义词unheimlich并最终与其重合,因此,unheimlich一词与其反义词的一层意义相悖,与另一层意义却非如此。
暗恐理论的评论者对于他们所说的东西同样存在困惑。两个词含义重合,却又互为反义词大概是一种罕见的语义现象。但是这种思想的其他表征证明了这种独特性:本杰明的辩证思想将对立置于张力中(现在/过去,古代/现代等),几乎是背对背的关系,就像是山阳和山阴(从这种隐喻中,得出了阴和阳的相互性);或者,再如黑格尔“扬弃”概念中的抛弃-保留如同两个对立面,既相互结合又相互对立——比如存在与虚无统一于变化中,但二者又被保留在差异中。
美学的两极性
现在,我来谈严格美学意义层面上的问题。说到“严格美学意义”,我所指的是一种情感,我们通过美学方式讨论的任何对象向我们提供的情感——言下之意:不是通过认知方式,尽管认知或多或少地属于美学的范畴(我暂且将这个历时已久的议题放在一边,之后再从侧面来进行讨论)。康德将其称之为快乐与不快(Lust/Unlust)的情感。以康德的观点,这种结合的确是纯粹出于规范;就像我们在第三批判的第9节中读到的,这位哲学家所寻求的“品味批判的关键”唯独与快乐相关,宁或是快乐的情感(因为,就像菲洛南科(Philonenko)所说的,“快乐的情感不是快乐;通俗地说,是我们从中获得的感受”9)。在开始讨论之前,需要理清一个问题,不快是快乐的缺失,还是痛苦?第二批判(《实践理性》)中明确提出了这个问题,因为快乐与不快的区别相当于好与坏的二律背反。丑陋之于美学范畴并没有邪恶之于道德范畴那般重要。
前面的内容已经向我们暗示了一种更为复杂的美学,不仅是三重意义的(在积极与消极之间还有中性),而且在多个方面是双重意义的。尤其是这种双重性可能会打乱知性和想象之间的自由变换,而根据康德的观点,对于知性和想象的意识是美学乐趣的关键。撇开关于各种能力的词汇,以便考察一下认知和情感的关系。适合的对象在这两者之间引起相互变换,在变换过程中,我们有时候会经受双重性的考验,这时,在分析过程中就会出现情感的意外激发,或者相反,某种情感给我们带来深入分析的紧迫性。
然而,我在本文中所谈到的并不涉及认知与情感边界处的这种特殊情况。我也不会详述美学价值观(中性、美、丑及其他)的困惑,然而鉴于这个问题涉及美学双重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是值得进行说明的,因为比起困惑的美学,我对美学的困惑更感兴趣(虽然……)。目前,我尤其想指出的是,这种困惑实质上存在于仅从美学态度本身考虑(并将之与认知的兴趣点区分开来,认知的兴趣点并不仅仅是补充成分)的空白中。其最清晰的描述肯定是在阿奇博尔德·艾里森(Archibald Alison)的《论趣味的本质和原理》(Essays on the Nature and Principles of Taste)10中,该文与《判断力批判》在同一年面世,即1790年。这不仅仅是一篇美学家的文章,即充斥大量具体事例并且参照其“品味”经验的文章,而且那种著名的无私快乐在文中得到尤其强烈的表达,因为它将这种概念所回顾的东西与其对立面相结合:抛弃一切非美学的趣味,并专一地投身于美学趣味。在美学情感中当然存在一种必要的两极性困惑,其中一极是思想完全被艾里森所说的“一种迷人的遐想”(a kind of bewitching reverie)11所占据,另一极是主动去寻求这种催眠状态,把心思集中于激发这种催眠的对象,以及寻求这种催眠所提供的快乐。
分析与综合
美学理论中最有趣的议题之一位于我们分别称之为综合和分析的两大倾向之间的分配层面上。综合的倾向主要关注美学体验的时刻,即将心思集中于体验对象,并从整体上考察这一事实。分析的倾向主要关注美学经验之于对象的工作,关注鉴别该对象细节的能力,并塑造一种鉴别该对象品质的更为细腻的能力。上述两种观点相对立的最好代表是艾里森-伯克这对组合,以及他们对于联想问题所采取的立场,前者支持,后者反对。我们的美学情感是否来源于我们按照其特性所考虑的对象直接产生的情感,或者来源于对上述对象的这种思考在我们的头脑中激发的“一连串想法”(a train of thought),从而形成一种遐想?
在这里并不是要对上述议题得出一个结论,但仍然要思考一种可能的两极性。为了赋予这一议题以新的角度(并且我在下面还要旧事重提……),我们可以采用现成物品的例子。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两类:未经雕琢的现成艺术品,即随手拿取的日常物品,并按原样展出;经过加工的现成艺术品,即艺术家对物品进行了这样或那样的干预。杜尚强调了这种“重要的特点:当我有机会的时候在现成艺术品上铭刻的短句。这个句子并不是为了起到一个标题的作用来描述这件物品,而是用于将观众的思想带向更具言语性的领域。有时候我会在介绍中增加一处图示的细节:我用这种方法是为了满足我对于叠韵的爱好,‘ready-made aidé(经过加工的现成艺术品)’(‘ready-made aided’(经过加工的现成艺术品))”12。我们可以给加工过的现成艺术品补充一句题词,非常清楚,这句题词是“用于将观众的思想带向更具言语性的领域”,或者说是更为诗意的领域,这句题词通过联想来发挥作用。在这里,联想的判断区别于简单的情境判断,情境判断是现成艺术品所暗示的,或甚至一种困惑,这种困惑产生于没有艺术身份的物品和它在特设制度背景下被献给艺术的事实之间的反差。这种困惑并不是同样的困惑:诗意的附加就像是一种焦虑的迷魂酒,即献给艺术的日常物品所激发的焦虑。
在其他情况下,这种迷魂酒来自于多多少少充斥于作品中的副文本——有时候,这些作品出现在一些后现代派的展览上,直至饱和状态——,或者它同样来自于我们随身携带的文化资本。面对令人焦虑的物品,除了情境判断和联想的判断之外,还存在类别的判断:按已知类别给事物贴标签的难题困扰着我们,上述类别属于这样一类,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其变故。但是,正如我们运用现成艺术品这一术语所提出的,物品很快便会找到其所属的类别;现成艺术品这个词深得杜尚之心,他到纽约一段时间之后听到有人说这个词,但又过了很长时间他才接受其作为一个类别。无论如何,实现归类之后最初的困惑得以缓解,但同时,令人焦虑的物品本身的性质意味着它还会产生后续影响。这正是一种抛弃-保留,因为类别本身就模糊不清。将种类概念深入其内心的行家可能感到乏味,但是新手在进入联想的过程从而掌握类别之前,可能会体会到犹豫不决的情感所造成的冲击。
最初困惑的清新感……
我们知道,杜尚把这个行家称之为“观察者”。是他自己在谈论清新感:
“我认为绘画正在死去,这你们懂得。画作在四五十年后将死去,因为它的清新感将会消失。雕塑也会死去。这是我自己的小达达主义,无人能接受,但这无所谓。我认为一幅画在数年后会像其创作人一样死去;接下来,这就叫做艺术的历史。一幅莫奈画作在如今已经黯淡无光,它与60到80年前的莫奈画作有着天壤之别,那时的莫奈画作刚刚画好,光鲜亮丽。现在它已进入历史,大家都这么认为,这也挺好,这不会改变任何东西。人总有一死,画作亦然13。”
杜尚谈论画作之死显然是在自欺欺人,提到莫奈的画作时更是如此。我们刚刚目睹的一场作品回顾展的成功就是明晃晃的反证。如果画作充满了遗产的韵味,它即使变得黯淡无光又如何,艺术的历史铸就了它的永恒,远远超出假设的过时日期……这并不算对画作的修复……仿佛有两大主要原因造成了清新感的衰退:一方面在于物品本身,一方面在于接受者,两者都在日渐衰老。这就是为什么艾里森认为年轻人对遐想更为开放。伯克认为,简单的快乐和解除困惑的能力属于年轻人,理性的快乐属于成熟的年龄阶段,而悲观则属于老年阶段:“在一生的早年阶段,感官还很稚嫩和新鲜,当整个人体被唤醒,当新颖的闪光给我们周围所有的事物注入清新感时,我们的感觉是多么强烈!但我们对事物做出的判断也是多么错误和不准确!如今在我看来浮浅且卑劣的作品曾在那个年龄带给我从未有过的创作天资和同等的快乐。14”
清新感与两个概念相关联:自发性和生命力。“捕获瞬间。自发性与清新感”,布列松在他的《电影书写札记》5中这样写道。马瑟·牟斯审视了不同的艺术,指出“音乐比其他艺术形式更具优越性:它包含着柏拉图所说的一种清新、一种迷狂、一种热情的奔放、一种真正的陶醉,在他之后,尼采和罗德(Rohde)也这么说过”16。至于绘画,我们经常会强调速写的清新、第一笔触的新鲜感……在自发性的背后,至少是一种生命力的奔放(本意上的)?因此,黑格尔将清新感与生命力相提并论:与荷马作品中运用的方法和物品相反,它们“直接来自于人类活动和自由(……),在文明社会中,这些物品取决于上千种外在因素,取决于一种复杂的生产方式,在这种方式中,人类自己变身机器,成为机器的奴隶。事物失去了它们的清新感和生命力;它们毫无生气,不再是人类自己的直接造物,在这些事物身上,人类喜欢自鸣得意,孤芳自赏”17。然而,生命力可能有多种成因,也有可能是人为原因。如果出现心力衰竭,我们会使用心脏起搏器……
为了进一步讨论这个话题,在此再一次分裂仍是有用的——这种分裂从模糊的中间部分开始进行辨别,开始作出定义。当我们谈到作品的清新感时,不管是丢失的或保留的清新感,我们会谈及一件成型的物品,就像杜尚所说的现成艺术品;当我们谈到美学体验的清新感,谈到它给我们造成的困惑时,我们所谈的是一种稍瞬即逝的现象,造成困惑是因为这种体验给人一种瞬间的印象,而在这时,思维却活跃起来。美学困惑的悖论,就在于我们在遇见一件貎似失去清新感的物品时突然感受到的这种困惑,还在于自发性的瞬间是以思维前期活动为条件,这或许需要一种文化资本的介入。然而也不能忽视意外的怦然心动,或多或少无法预料的心动。相遇和意外不断加强着困惑:这不能让你想起点什么吗?
第二种方法:从艺术和艺术家谈起
在杜尚和令人焦虑的物品的问题上我们遇见了一个门槛。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是否从其固有的功能方面谈论美学体验——这是抽象的,正如康德所希望的,谈论由客体确定的决定性——或者相反,我们是否考虑这样或那样的配置可能对美学体验产生的效果,一种人们觉得或多或少是决定论的效果。美学的困惑现在已经不仅仅是潜在的接受者所探究的东西,而是艺术家本人所探究的东西,或者是他有意建立一种明确的因果关系,或者是让接受者以或多或少自由的方式欣赏这种困惑的效果,这要参考多种可能的原因,或者没有可识别甚至可想象的原因。我现在将考察美学困惑的若干形象,这是从艺术态度及其影响中归纳出来的形象。
创作的困惑
首先,创作的困惑给艺术家们启发了许多美丽的篇章,他们把创作归功于灵感。这时就涉及到创作学的问题,这一点不可小觑,因为除了它所呈现的内容,或具体或大略的细节,这同样涉及到他处的问题,涉及到多少有些模糊的彼世。由此产生了一种二重性,从心理学上看,这种二重性可能会影响到艺术家的人格本身。艺术家可能感受到的是一种人格的双重性。再回到心理学方面来,我们今天称其为身份分裂症,其定义为“出现两重或多重身份或者是不同的‘人格状态’,它们轮流控制患者的行为”;但要明确指出,“我们承认并且了解,某些文化范畴的活动或者某些宗教体验也可以用分裂状态来解释。它们本身不是病态,尤其是它们不会带来明显的痛苦,也不会造成机能的恶化”18。好消息,艺术家可以逃脱精神正常状态的看管!
我们还是不相信他能完全处于标准状态,这位艺术家就像是被另一个人,另一个他所占据,对柏拉图而言是神妙幻想的受托人,或者像兰波那样大喊出:“自我即他者19。”这句话值得一番注解。话中可能想表达作为艺术家的自我是在他之外的另一个人,或者是作为艺术家的自我是作为个人的自我之外的另一个人。换言之,这个自我参照于作为自身存在的普通意识,在这种情况下,相异性相对基本的自反意识得到定义,或者参照于由艺术家作品塑造的自我,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涉及到作品中的自我与个体的自我相互区别的方式?自我作为艺术家是他者,或者是艺术的自我是另一个个体的自我。他者是否存在于个体之中,就像是对其反向意识的侵入,通过他作为艺术家所完成创作的回馈侵入,或者他是否存在于个体之外,就像是创造出了一个复体的人,多多少少有些幻化的复体,这是一种分身,可能除去凶相的方面?让·保罗(Jean Paul)将分身赋予“那些看到自己的人”(《齐本克斯》,1796年)20;艺术家看待自己就像是看待另一个人,但是这个人却附着在他的身上,不仅像是他所物化的某个事物,而且还是他主观性的组成要素,成为他自反意识的持份者。创作的困惑意味着这一点,即兰波表述的两种解释都需要重视。这就是它与暗恐平衡之间的关联。
美学的困惑
我已经暗示过,美学和创作学的时刻,当它们指两种实践立场和社会立场时,观众的立场和创作者的立场时,两者之间的区分好像并没有看上去那么清晰。尤其是在创作本身的空洞中也明显存在美学的时刻。在上文引用的《美学讲话》中,保尔·瓦莱里提出了一种考究的思想,即在美学(以此为名的学科)自身的范畴内,区分出两个领域:一方面是“美学(esthésique)”(这个词最接近词源:asithèsis),即来自于敏感性方面,另一方面是“创作学”,这与创作有关,与创作行为有关。
这是因为从自我到自我即他者的循环,即刚才探讨的问题,它并不局限于问题本身。因为还有外界的存在,同时有世界和作品,以及周围的世界和作品的世界。创作困惑的另一个方面是艺术家与世界的关系所进行的双重协调,还有他在作品中写入协调符号的方式,这些符号使作品及其接受者之间的协调成为可能。因此,实际上这是三重协调……在这一点上,我们又想起了兰波及其著名的“感官失调”。这种表述显然具有挑衅性。它提及到某些非正当物质的困惑,其结果会产生我们今天所说的“改变的意识状态”。我们不想再回到上文提到的人格障碍(也称之为人格解体)上,这里令我们感兴趣的是美学的困惑,且不说它那或多或少已经探究的原因或者它对意识所起的作用。
这并不仅仅是一些极端的体验,而是一种感性的实验,以及该领域的扩展,这个领域以绘画这样简单的事物开始:一块与外部世界分离的封闭场地,在任何叙事与道德之外,这里的可见物在画笔下熠熠生辉(就像我们所说的,窗玻璃在阳光下闪耀)。在画作之外,这种实验得到扩展,根据不同的情况,延伸至有可能作为艺术载体和新型感觉传递者的客体系列。我们从中可以感受到诗人所说的错乱,但同样会从中寻找并发现一种对世界与美学关系的再认识。皮尔士说,艺术家的美学才能是“难得的才能,它能让人看到眼前的事物,就像事物自我呈现一样,不需要任何其他阐释的替代,也不需要考虑这般或那般情况的复杂程序”21;皮尔士给艺术家赋予一种精练的能力,即使不是艺术家,通过训练也能达到这种能力。况且还需要艺术家那经过训练的眼睛,倒不是去看直接的世界(皮尔士所说的“现时性”),而是去看这个世界中可能的艺术,否则就没有任何从世界符号向艺术符号的转变。这种转变的对象也可以是艺术本身,就在艺术回到世界中之后(在作品创造之后):这就是康定斯基看到莫奈的《干草堆》时所产生的困惑,因为在绘画主题之外,他还看到了形式。
本体论的困惑
康拉德·费德勒(Konrad Fiedler)对于我方才论述的观点似乎持反对意见。他说,所有人都能对事物有另一种看法。“艺术家并不以其与众不同的观察天赋而出名,他并不会比他人看得更多,也不会比他人印象更为强烈”,而是通过其卓越的“表达”22得以出名。我方才通过康定斯基的例子提到的决裂,费德勒将在感知和表达的非连续性中找到它;如果我们具备与艺术家相同的接受能力,我们却不能进入创作的行为;艺术家带来了“感觉的价值,还有意义本身的价值”23,因为他的意识以其独特的表述自行投射到作品中;真正的“艺术文化”,对于非艺术家而言,就在于“得到这种针对世界的特殊意识的熏陶,而这种意识会存在于艺术家的作品中”24。
然而这一结论将我们带回到前面提到的两种困惑。灵感带来的究竟是什么,它的结果是什么,它的目的性又是什么?瓦莱里说,“通俗意义上所说的”灵感就是这个时刻,此时的艺术家蜷缩在创作学中,并且沉迷于“兴奋无比的身体”中;这是“一种让我们处于自身之外或远离自身(……)的状态,而在这种状态中,不稳定却支撑着我们”;然而尤其是它能给我们提供“另一种存在的念头,这个存在完全拥有我们自身极其罕见的能力,完全由我们能力的临界价值构成。25”我们看得很清楚,这里就像是一条困惑链的构成:灵感激发的冲动,持续的不稳定性,本体的创作。兰波说的并无二样:“所有感官那长久、宽广和理性的错乱”不仅将艺术家的身心带入它的漩涡,而且指向一种本体论的创设,即寻找新世界的诗人通灵者的创设:“难以形容的折磨,其中他需要整个的信仰,整个的超人力量,他在所有人中间变成重病人、大罪犯、被诅咒者——以及无上的智者!——因为他到达了未知境界26!”
结构的困惑
如果要确定本体论的维度,就得求助于艾提安‧苏利欧(Etienne Souriau)对艺术所做出的两种无以取代的区分,即存在两种艺术,一种称之为表现的艺术,即在作品和它所表现的虚构人物之间“存在一种本体的分离”,另一种则是介绍的艺术(présentatifs),即“作品和对象融为一体”27。大家都很清楚,绘画或电影属于前者,音乐属于后者。我们也可以认为这是两种方式,而且表现的艺术也可以是介绍的艺术(相反的情形只能模糊地表现其真实性,比如在回顾一种思想或某个故事的音乐中)。在许多作品中,形式不仅仅是讲故事的外衣,而是在与其他要素(材料或意义)的互动中承担着发生角色,这时的介绍方式将会搅乱表现方式。这就是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Victor Chklovski)在其“陌生化(ostranenie)”概念中所要表达的东西,这个“奇特的表现”手段使得作品形式及其接受变得更为复杂28。
我把结构的困惑称之为一种矛盾情感,即作品的方面或瞬间所产生的情感。在这部作品中,作品与对象的融合通过主导的介绍形式(并非唯一的形式)展现于结构中,也可以说展现于在作品的成文中。其例证在多种艺术类型中层出不穷。在文学方面,萨缪尔·贝克特在其惊人的《最糟标记》(Cap au pire)29中达到了结构困惑的极限:
“首先是物体。不。首先是地点。不。首先是物体和地点。时而谈前者或后者。时而谈后者或前者。厌倦了前者再尝试后者。厌倦了后者再回到前者。周而复始。再度变得更差。直到同时厌倦了两者。呕吐然后离开。那里既没有前者也没有后者。直到也厌倦那个地方。呕吐并且回来。还是那个物体。那里什么也没有。依然是地点。那里什么也没有。再试一次。还是失败。失败得更多。或者是更惨。失败得更惨。比更惨还要惨。直到真正地厌倦。真正地呕吐。真正地离开。那里确实既没有前者也没有后者。真正地一劳永逸。”
在这种散文式诗歌中,即由既重复又有差别、既并列又交叠、既有近距离顺序又有遥远呼应的只语片言构成的诗歌中,一块语义丰富的布料慢慢织成,既没有披上所期待的“恰当对象”的话语形式,也不容许终结意义所导致的写作放纵。
概念的困惑
“这是概念作品!”如今我们经常听到这种话,来谈论当代艺术“作品”,但是它与概念美术没有任何真正的关系。事实上,这仅仅是一些艺术主张——作品、半作品、非作品或作品戏仿——它们是某个概念的展示。就这个话题,重要的是要阐明一个看似模糊的境况,至少对某些人来说是这样。同样重要的是要考问,这种展示概念的艺术所突出的东西在何种程度上可以激发一个美学评判,言下之意,通过这种美学评判,我们在此假设必须理解这个或多或少表达的评判类型,这个评判将显示一次不太可能相遇的困惑。
如果说历史意义上的概念美术与某个概念有什么关系,那就是与美术概念有关联。它要求创作者的全部整体意识,而通过反馈,又要求接受者的意识,原因是人们在展览地点展出的东西,即人们在信任的地点展出某件作为艺术的物品,它只是一个艺术试展品,是艺术定义的一个建议。它还要求艺术家把精力集中在这一关键事实上,与所有可能转移他注意力的东西决然不同。因此便有了对任何美学附属物的抛弃,以便专注于艺术作品,按照它所倡导的艺术定义,按照关于艺术的重言逻辑。在这种情况下,概念的困惑主要是认知的,局限在我们了解(承认)的艺术范围之内。
关于概念的展示,其困惑有所不同。这里动用的概念不再直接是艺术的概念,而是作品的概念。作品之前便有概念领先,而对于观众而言,作品朝着概念的方向缩减。如果说将康德对于认知和想象的游戏诠释为一种必要美学困惑的理论是恰当的,那么我们同样可以相信哲学家康德的做法,即预先知道概念的艺术性展示的效果,这时他预先告之,人们鉴定为概念的任何作品,将结束游戏的角色赋予认知的作品,它会阻碍美学的情感,与之同时受阻的还有快乐。那么困惑的本质则可能变成我们面对艺术却感受不到快乐的事实。概念的展示与概念艺术不同,除非对艺术鉴定产生怀疑,否则便不会质疑艺术的定义。有必要再次强调这两种形态,它们相互背道而驰,一种是向心的,将艺术紧扣在其定义上,另一种是离心的,使艺术散播在文化之中,然而两者经常被混为一谈。
人们还可以谈论概念的展示和焦虑的物品之间的混淆。只需读一下超现实主义的作品,比如安德烈·布勒东的《物品的危机》30,就可以设想分离两者的矛盾对立。令人惊奇、令人担忧、模棱两可、令人焦虑的物品改变了功能——诗人布勒东说是“角色的变化”——,并不是要联接一个将上述物品带回其客观性场地的概念,而是要通过简单选择或玩弄能力,去获得一个想象的维度——诗人所说的一种“回想的能力”。
只言片语充当总结……
困惑似乎是真真切切的,且存在于多个方面,与两极性有关……
通过两种考察方法之后,我终于到达同一个对象:令人焦虑的……
应该区分概念和类别:令人焦虑的物品在概念上是模棱两可的,但在类别方面并不含糊;对于概念的展示,情况则相反。前者令我们困惑,因为它属于艺术的范畴,后者令我们困惑,因为我们不再清楚它是否属于艺术的范畴……
美学的困惑遇上了困惑的美学……
美学和艺术学错综交织在一起,却永远不会融为一体……
最后,这纯粹是个预见性观点:我们可以从创作过程之外的另一个途径回归艺术家的困惑,那就是艺术家社会角色的途径。艺术家,困惑的制造者……